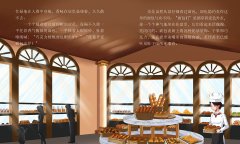《小伞兵回家了》第15章
多么宁静的夜晚。
黑纱笼罩着的大地,在朦胧月光下,处处留着斑驳的影子。
万物都多了影子的陪伴,就伟杰,没有。
月光没洒进他的窗里。
门外,隐约传来家人的谈笑风生,自己却怎么也挤不入他们的谈话氛围中;自己躲在房子里,无来由的空虚感充斥了整个心灵。
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的......寂寞,孤独。
伟杰禁不住这么想: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吗?有家人在身边却等同于没有一样,他们跟我是如此接近,却又那么遥不可及。以前嫌弃阿婆麻烦,现在没有她在耳边啰嗦,又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了;以前虽然不喜欢那见面就吵架的爸爸,现在爸爸对我像朋友一样,我却感觉难以亲近了,因为他总不把我当儿子看待。妈妈对我,感觉更远,她不再宠我、抚摸我的头......
“嘶嗦......嘶嗦......”
咦,那一闪而过的是什么?
好像是人影!
“外面有人!外面有人!”伟杰吓得跳起来,跑出去告知大家。
大家一窝蜂涌出去看个究竟。在房子四周找了找,看了又看,都没有收获。
“会不会是你看错了?”爸爸问。
“不可能!他的确经过我的窗前!”伟杰接过爸爸手中的手电筒,往丛林间再照一照。
公公从另外一边走过来,说:“没人哪!”
“没有理由!难道我见鬼了?”伟杰喃喃自语。
婆婆竟笑起来:“呵呵!你一定是平日亏心事做太多了,人家没半夜敲门,你就已经心惊胆战了!”
“哈哈......”
“呵呵......”
伟杰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,跟随他们进屋里。
妈妈递上一杯水,说:“喝杯凉茶定神吧!”
伟杰喝了一口,问:“蒲公英加车前草煲的凉茶吧?”
妈妈有些惊讶:“你喝得出味道来?”
“我妈妈常常煲给我喝,她说是阿婆教的。”
“真巧!”妈妈指着婆婆笑言,“这也是‘你的阿婆’教我的!”
“我教你的东西可多呢!”婆婆搭话,“咸鱼焖肉,腊肠炒豆芽......”
“夜香花煎蛋,既简单又好吃!我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!”伟杰兴奋地插口。
“真的吗?”婆婆感到很意外,“我儿子阿财也爱吃哦!”
爸爸也爱吃夜香花煎蛋吗?怎么没听妈妈或婆婆说过呢?每次妈妈煮了这道菜,爸爸只吃那么一点点儿,剩下的全由他“收拾”。
“听到都要流口水了!明天就去菜园采些夜香花回来煎蛋,好吗?”爸爸拥着妈妈央求着。
妈妈捏了捏爸爸的鼻尖:“好吧!馋嘴猫!”
爸爸好肉麻!在伟杰的印象中,爸爸从没有如此孩子气过。是不是爸爸被他气得变老了?还是生活压力让爸爸失去了年轻的心境?
伟杰心底不禁涌起酸酸的感觉。
婆婆捧了一碗汤,放在桌上,喊妈妈道:“阿英,把这碗泡参汤喝了,凉了才喝对身子就不好了。”
“遵命!”妈妈笑嘻嘻地端起碗,对婆婆说,“谢谢,妈。”
“多喝些补身子,生出来的宝宝就健康、好照顾!”
婆婆说,“坐月子要用的东西,你叫阿财买齐了吗?”
“嗯。还差党参,那天去买时,药材店的货卖完了,还没进货......”
“对了,入院前要准备的衣物,你都准备了吗?不要忘了把乌金丸和追风丸也一起带上,那是在医院生产后要吃的......”
婆婆和妈妈开始谈起坐月子的事了,伟杰不好意思也不方便插嘴,只得静静坐着。转头看看公公和爸爸,他们正在谈论着发展果园的事。
“多几天,我去市区买除草剂回来,能快些把杂草清除。”公公说。
“我去买吧!这里去市区三十哩,你眼睛不好,骑摩托车去太危险了。”
“没关系!我认识那老板,方便讨价还价。你比我壮,动作快,所以你还是留下来快点儿把杂木清除!我这副老骨头,帮不上太多忙,买除草剂这样简单的事就由我来做吧!”
“可是,我还是不放心......”
“你少担心了!这辆老铁马跟了我三年了,我还不熟悉吗?三十哩的路又不是新路,你问你妈妈,我以前骑脚踏车载她下马六甲游玩,多浪漫哪!你妈妈都没害怕过呢!那时......”
“爸,你有没有夸大呀?从这里去马六甲,驾车要一个小时半,你骑脚踏车都要骑大半天了!就算去到那里,你哪里还有力气谈恋爱呀?哈哈!”
“我骗你又没奖金拿,骗你干吗?你不要忽视爱情的魔力,它可让我冲劲十足,歌词都这么唱:‘爱情路千万里,我也要......’”
“天哪!爸唱情歌了,怪肉麻的......”
伟杰望着公公和爸爸俩聊得起劲,笑声不绝于耳,一点儿也不做作,没半点儿虚假。他怎么也想不透,自己和爸爸怎么就不曾如此和谐地聊过天呢?每次爸爸从果园里回来,吃过晚饭,就在客厅里翻看报纸,他则在客厅里看戏,两人好像两樽雕像,各有各的精彩。像现在这样欢愉的气氛,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俩之间。是否因为爸爸压根儿没有想过要与他闲聊?还是自己所谓的叛逆破坏了他和爸爸之间的关系?
“哎哟!”妈妈突然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喊了一声!
“怎么?阵痛了?要生了?”爸爸一个箭步赶到妈妈身边,紧张兮兮地护着妈妈。
妈妈皱了一阵眉头,深呼吸后,笑着说:“不是啦!肚子里的孩子踢我呀!”
爸爸低下头,摸着妈妈的肚皮,轻声细语地说:“宝宝,你别坏蛋哦!改天你出来后爸爸就打你的小屁股!你要疼妈妈,妈妈怀你好辛苦,知道吗?”
“看!他又踢了!他嫌你烦,不要听你的话了!”
“没有的事!宝宝在回应我呢!”
伟杰发觉自己身上的肌肤有种被轻轻抚摸的感觉,柔柔地,很......很温暖,让他的心莫名安定下来。
啊!严肃的爸爸原来也能如此温柔。
爸爸是爱宝宝的,也应该爱他的,不是吗?


















序章
你们玩过“伦敦铁桥垮下来”的游戏吗?
你们当然玩过,这是一个至少需要三个人玩的游戏。其中两人面对面站着,双手高举交握,形成一座坚固的拱桥,让第三个人从桥底下安全地穿过。
我的问题是:当你们玩着这个游戏的时候,难道就没有得到什么启发吗?
——邢远洋
第一章
“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,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 my fair lady......”
这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五下午,时间是两点半正,温暖的阳光像一层牛奶膜落在一栋砖红色的哥特式城堡的建筑上。城堡的主建筑中央悬挂着几个大字:伊丽莎白中学。
此时,欢乐的歌声像流水般正从城堡的某一间课室内溢出。这间课室位于主城堡二楼尽头最偏远的课室,木门紧闭,门外挂着一个字迹模糊难辨的牌子:童谣社社团办公室。
仓促的奔跑声在走廊上骤然响起。
“砰”的一声,有人冒冒失失地闯进门来。
“对不起,对不起,我迟到了!”
闯进来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。她有一双小鹿一般的长腿,健康的小麦色肌肤,偏褐的短发微微卷曲,双目明亮如朗星,看上去神采奕奕,活力十足。
“咦,没有人吗?”
女孩左顾右盼,发现这是一间很小的课室,左右两边都置放着几个高低不平的三层柜,杂乱无章地叠着一堆书,中间是一张木桌和一块破旧不堪的白板,白板正中被人用蓝色麦克笔画了一条虚线,剖腹而过。地板上也用粉笔画了虚线,把课室分为左右两半。
其中一个矮柜上放着一个收音机,重复播放着《伦敦铁桥垮下来》。
“我是不是进错社办了?”女孩自言自语。
就在这时,她瞥见左边有物体动了动,才发现旁边一个三层柜边坐了一个人。
“嘿,你好?”
阴暗处坐着一个男生,他抬起头,木无表情地看了女孩一眼,又埋首书中。
“对不起——”女孩还想说什么。
课室门再次被打开。进来的是一个矮个子男生,戴着圆框眼镜,头发浓密得像戴了假发。看见女孩,他似乎呆了几秒,脸上随即浮现孩子气的笑容。
矮个子男生随手关掉收音机:“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?”他有一副高亢嘹亮的嗓子。
“你好,我是童谣社的新社员,今天第一次来报到。”
“新社员?”矮个子男生双眼放光,掩住嘴巴,“老天,我不是在做梦吧?真是谢天谢地!”
“啊?”
“哦,忘了说,我是童谣社的社长。”他说,“我叫高原,青藏高原的高原——虽然我的‘海拔’挺低的。” 他愉快地摸摸自己的头顶。
女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,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礼: “啊,对不起。”
“请问你是——”
“哦,忘了自我介绍。我叫邢星,是上个星期才从英国转来的学生,就读初二二班。现在加入童谣社,请各位多多指教。”她向高原粲然一笑。她的嘴巴稍嫌宽大,衬得牙齿雪白整齐。她也许长得不够标致,但是笑容绝对耀目。
“彼此彼此。”
“对了,其他社员还没来吗?”邢星左顾右盼。
高原脸上的线条变得尴尬起来,他咳了一声:“不, 已经到齐了。”
邢星环视课室一圈,目光落回高原脸上,咽下口水:
“社长您的意思是,童谣社连你我在内只有三名社员?”
“错了,只有两名。”高原摇晃脑袋,严肃地举起两根手指,“你和我。”
“那——他呢?”
“哦,那家伙啊,他是曾经加入童谣社一年的‘前社
员’。”高原用一种只有在熟人之间才会用的看似轻蔑实则亲昵的语气说,“目前是推理小说研究社的社长。因为课室不够的关系,课外活动处主任让我们两个比较低调的社团共用一个社办,看到了吗?地上那条虚线就是间隔—— 当然,这只是暂时性的方案,等童谣社声势壮大以后,我们就可以向主任要求比较大的课室。”
邢星不知道该说什么,她相信自己此刻脸上的表情一定相当复杂。
“别担心,我们的社员数量绝不是最少的。”高原安慰她,“至少比隔壁那家伙多一倍。”
邢星啼笑皆非,这么说来,推理小说研究社只有社长一名社员了。
“可是社员这么少,难道不会倒社吗?”
“只要在一个月内招满三人就行。”高原忽然担忧地问,“嘿,你不会想要临阵退缩吧?”
看着一脸沮丧的高原,邢星笑了起来:“当然不会。我对这个社团很有兴趣,也很喜欢唱歌,虽然唱得难听。以前的同学都叫我‘音乐盲’。”
高原如释重负,眉开眼笑地说:“哦,你的声音挺好听的,唱歌大概也不差。正好按照本社的惯例,新学员入社一概要当众高歌一曲的。你挑一首你会唱的童谣唱吧。”
“好啊。”邢星也不扭捏。没想到一开腔,就像一把 走调的小提琴,呜哩呜哩拉得荒腔走板,节奏忽快忽慢,音准匪夷所思。
一曲甫毕,不但高原目瞪口呆,连隔壁一直埋头看书的推理小说研究社社长也不禁抬起头,用一种看天外来客的眼神看了她一眼。
邢星有点不好意思:“我是不是吓到你们了?我说过了,我唱歌真的很难听的。”
“还真是……技惊四座。”高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 搜索枯肠挑选适当的措辞,“你把《小星星》唱出了重金属摇滚的味道,挺有创意,还有进步的空间!”
“谢谢社长。”邢星微笑,“那大概是受了我爸的一点熏陶,他很喜欢音乐的,对摇滚乐也略有研究。”
“是吗?呵呵。”高原干笑两声,笑声透露了他打死都不信邢星会有个音乐素养高的父亲,“今天是第一天, 我们早点下课吧。”
“啊,那么早?”
“我要去和主任求情,让他宽限找社员的时间。这样吧……”
他从那个小而乱的矮柜摸出一张发黄的纸张,递给邢星:“这是作业。你把五线谱写成简谱。”
“可是我看不懂五线谱……”
“问推理小说研究社社长。”
高原抛下这句话后,门就砰地合上了。
邢星无奈地转头看向推理小说研究社社长。他正在忘我地低头看书,仿佛周遭一切都是一团空气。
这人身上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,还是不要轻易靠近的好。邢星心想。算了,我还是靠自己把这堆豆芽处理好。
走出童谣社的社办,邢星到宿舍整理好行李,就拎着背包,穿过拱廊,进入主校舍,再一路穿行到学校大门。
穿过洞开的橡木大门,两旁皆是修剪整齐的如茵草坪, 错落有致地种着美丽的风铃木,中间是一条十英尺宽的人行步道。
清新的空气立即扑面而来。
校园真美,坐落在一片小树林内,放眼望去,一片绿意盎然。伊丽莎白私立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栋城堡式的学校。由三座城堡连成。中间大城堡为主校舍,宽敞阔朗,一共有三层楼;左右两小城堡只有两层楼,小巧雅致,一座充作男女宿舍,另一座则是图书馆。城堡的建筑风格为哥特式,以红砖砌成,在鲜艳的蓝天下分外典雅。由于位于半山,加上隐于草木之间,连空气也显得格外幽凉。
走在这样的校园中,有一种奇异的穿越感,仿佛置身十二世纪的欧洲。
邢星曾经听爸爸说过,伊丽莎白城堡建于五十年代,
它的设计师兼原主人是一名来自爱尔兰名叫赫伯特·乔治·伊万斯的绅士。伊万斯是一名艺术史博士,博学多才,兴趣广泛,具有极其新颖活跃的创造力及想象力。他在文学艺术、音乐、建筑乃至机械设计方面都有所涉猎。
后来,因为伊万斯博士的女儿伊丽莎白·伊万斯猝逝, 他在伤心之余决定返回家乡,把城堡以半转赠的方式卖给一名本地好友。这名好友后来在因缘巧合下,把城堡发展为私立中学,为了纪念暨感谢好友,学校遂以伊万斯博士的爱女之名命名为“伊丽莎白私立中学”。
邢星为能够在这样美丽而充满书卷气的校园读书而感到幸福。以前在英国,她不止一次听爸爸缅怀这所他昔日的学校。而爸爸口中描述的校园美景,竟和眼前一模一样。
可惜爸爸已经不在了。
邢星站在校门口,望着巍峨的校园,想象爸爸理平头, 穿着校服的样子。
爸爸是在两年前因脑癌去世的。一直到最后一分钟, 他都在勇敢地和病魔战斗。
打从邢星出生以来,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英国利物浦。爸爸在一家船务公司当工程师。妈妈则是医院护士。爸爸从日本大学毕业后到了英国工作,结识了在那里留学的妈妈,结婚后就在那里落地生根。
之所以在船务公司工作,是因为爸爸很喜欢海。连他的名字“邢远洋”都和海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爸爸还说海浪拍打岸边是有韵律有节奏的,就像音乐一样。
爸爸也很喜欢音乐,每逢周五和周末,他都会到一家小酒吧充当一支业余摇滚乐队的电贝斯手。在邢星眼中, 爸爸抱着吉他的样子总是散发着一股迷人的魅力。可妈妈对摇滚音乐一点也没有好感,认为摇滚乐是“来自地狱的噪音”。所以爸爸在家里唱的都是民谣。
一首一首的西洋民谣从他手中的吉他流泻出来,配合爸爸低沉温柔富磁性的嗓子,听得邢星如痴如醉。
长大以后,爸爸告诉邢星,她刚出世不久,只要一哭闹,爸爸一弹《Twinkle,Twinkle,Little Star》这首歌, 邢星就会破涕为笑,万试万灵。
“所以,我就帮你取名邢星,听起来就像星星一样。” 爸爸笑说,“这首歌就是你的主题曲。”
“那爸爸有没有主题曲呢?”
爸爸侧头半晌,笑道:“有的。爸爸的主题曲是《Lon-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》。”
“为什么呢?”
“这是一首友谊之歌。”
“什么是友谊之歌?”邢星锲而不舍地追问。
爸爸尚未回答,经过的妈妈已经忍俊不住地大力搓揉邢星的头发:“星星,你真是个问题儿童!”
爸爸去世后,邢星和妈妈开始两人生活。妈妈是个独立而坚强的女人,心态乐观。但是,从去年开始,奶奶就不停催促妈妈带邢星回故乡居住。妈妈认真考虑过后,便询问邢星的意见。
“你想留在英国,还是回去爸爸的故乡陪奶奶?”
以前在英国的时候,爸爸每隔一两年就会带邢星回来这里探望奶奶和姑姑,所以邢星对奶奶和姑姑并不陌生。她无比怀念奶奶的手艺和姑姑的笑话。
她只想了三分钟,便做了决定:回故乡。
衣食住行安排妥当之后,妈妈开始询问邢星想要就读
哪一所学校,她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伊丽莎白私立中学。” 因为那是爸爸的母校。
穿梭在校园中,邢星回忆起爸爸,虽然无比想念,但是那种灼人的悲伤已经不再。她相信,爸爸的回忆像粒子一样散落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,在阳光中闪耀,在泥土中滋长,随雨点飞溅,随花粉传播。她站在这里,时时刻刻都可以和爸爸共享,伸手就可以触碰。
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邢星很快走到小路的尽头,看见一辆黑色的四轮驱动车停在面前。驾驶座的玻璃镜慢慢滑下,浮现妈妈爽朗的笑脸。
“嗨,怎么样?开学第一个星期,还习惯吗?”
邢星打开车门,跳了进去,笑嘻嘻地说:“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校园实在太美啦!妈妈你呢?第一周上班还习惯吗?”
妈妈从上周开始在一家私立医院当高级护士。
“那还用说?那些菜鸟护士都称赞我打针的技术一流, 小娃娃还没来得及哭就打完了。”妈妈得意地说,“对了, 刚刚远远看你走过来,好像又长高啦。”
“真的?那太好啦,我希望十六岁就可以长得像爸爸一样高。”
“那你将来只好找个打NBA的当男朋友!”妈妈说,
“今天我临时要值晚班,所以我们先去奶奶家吃晚饭,然后你在那里过夜,明天中午再来接你,怎么样?”
“太棒了!”邢星笑逐颜开,“我好久没看见奶奶和姑姑了。”
“是啊是啊,整整一个星期了,真的好久呢!”妈妈用滑稽的语气说。
“哈哈哈哈!”


《2042年——背包里的天空》第一章
“把背包放在地上!”
我坐在椅子上,双腿禁不住打哆嗦。我不敢抬起头来,只看见护士阿姨的白色大褂,还有白色布鞋。
我一直以为护士阿姨是那种说话轻轻柔柔、举止斯斯文文的女人。可是眼前这个护士阿姨,对我说话有一点儿粗鲁。她这一句话,就像一条鞭子,对我抽打,吓得我闭起眼睛。
护士阿姨,我真的很害怕。
“小朋友,你听见我说话吗?把背包放在地上!”护士阿姨大吼。
听见。不只我听见,全部人都听见。医院的大堂里,有这么多人。护士阿姨,你这么大声一喊,谁还没听见?
他们都会转过头来,瞪大眼睛看着我。
护士阿姨,你叫我该怎么办?
我勉强忍住,憋住快要掉下来的眼泪。我很想放声大哭,但我又不想丢人现眼。
这么多人,这么多人!
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人,从来没有让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。我发怵,我彷徨,我无助。人的眼睛,十分可怕,我受不了,再也受不了。
求求你,护士阿姨,别再理我。
护士阿姨非但没有走开,还步步逼近。
听见她的呼吸声,我侧身避开。
她不放过我,伸手过来,拉我的背带,企图把背包拽起来。
“你背着一个大背包,不辛苦吗?你不辛苦,我看了都辛苦。你把大背包放下来,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吗?”
我攥紧背带,不让她把背包扯开。
她使用暴力,强硬地把背包提起。
我的屁股一凉,离开椅面,整个人连同背包已经被她提起来。
这么多人在看着我,我的脸不知道往哪里放。眼泪控制不住,簌簌流下。
“你这么轻?你没吃饭哪?”
护士阿姨松手,我和背包跌落椅子上。
“唉,没有看过脾气这么犟的小孩子。哭?还哭?”
护士阿姨把我弄哭,总算达到她虐待儿童的目标。她对我狞笑,搓搓双手,踏着胜利的步伐离去。
我低垂着头,眼泪吧嗒吧嗒滴在地上。
一个人在公众场合,我没有安全感。
要是狗狗在我身边就好,偏偏狗狗又不在。医院不让狗狗进来。
妈妈,妈妈,怎么你还不出来?你怎么能够丢下我一个人在大堂里?
不要哭,我不要哭。我得冷静下来,理智地想一想,到底发生什么事。
这件事最好跟斑鸠无关。
我担心的是,斑鸠会传染禽流感。可是没有听过斑鸠会传染禽流感,妈妈是兽医,也没有听过。
这两年,禽流感来势汹汹,名堂五花八门。去年2041年,禽流感叫做H4N11。今年2042年,禽流感叫做H4N12。
去年禽流感由乌鸦传染,特攻队砰砰砰把乌鸦和黑色的鸟全杀死。今年禽流感由鸽子传染,特攻队又砰砰砰杀死鸽子。
特攻队的处理方式,妈妈并不认同。妈妈认为控制禽流感应该有其他办法,不应该滥杀鸟类。人家说,医者父母心,妈妈是兽医,有禽兽的父母之心,于心不忍。
这么说也不对,如果妈妈是禽兽的母亲,我岂不是成了禽兽?就当我半个禽兽吧。那只飞来的斑鸠,我看了深表同情,犹如见到同类。
那只斑鸠,昨天悄悄飞到我家车房来,等待妈妈放工回来。它似乎知道我妈妈是兽医,扑上门来求救。它带伤而来,翼翅被枪弹射中。大概特攻队误把斑鸠当鸽子,对它下毒手。
别说特攻队糊涂,我也认不出。鸽子和斑鸠,看起来差不多。我开门迎接妈妈,狗狗跟在我身旁。狗狗嗅觉敏锐,发觉缩在墙根的鸟儿,告诉妈妈。妈妈走过去,躬身仔细观察。我叫道:“妈妈!小心!鸽子!禽流感!”
“这是斑鸠,不是鸽子。”
“斑鸠?”我走过去,看个清楚。
妈妈喝道:“风起,你走开,不要过来。”
我后退几步。“你又说不会传染?”
“虽然没听说过斑鸠会传染H4N12,不过,还是要小心为是。人家叫斑鸠作野鸽子,叫原鸽作鸽子。斑鸠跟原鸽不同属,斑鸠是斑鸠属,原鸽是鸽属,却同样归类在鸠鸽科之下。所以,现在我问你,为什么要小心?”
妈妈没有忘记机会教育,把握机会教育我一番。妈妈也是我的老师,她教过我分类学,让我明白什么是界、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。她每次教导我过后,都会提出一个问题,考核我的理解能力。
这么简单的东西,我一听就懂。我复述她教我的东西:“斑鸠是野鸽子,原鸽是鸽子。斑鸠是斑鸠属,原鸽是鸽属。斑鸠属和鸽属都同样在鸠鸽科之下,就是说,斑鸠和原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原鸽会传染H4N12,斑鸠也有这个可能性,所以,我们必须小心。”
“很好。”妈妈很满意我的答案。
我也很满意妈妈的称赞。
妈妈给斑鸠治疗,不准我和狗狗靠近,坚持要我和狗狗站在三米的距离以外。她也采取防范措施,戴口罩和手套,洗手消毒。
她把斑鸠救活,自己却染病,昨晚一夜咳嗽。
今天早上醒来,妈妈说她感到晕眩,悠悠忽忽,四肢无力,叫我们送她来医院。
我扶妈妈上车,妈妈的身体烫热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,输入医院的地址。狗狗坐在驾驶座上,陪我一起送她来医院。
医院外挂着一个牌子:“禁止携带宠物入内”。
狗狗不理,要跟我一起陪妈妈入内。
医院保安人员把我们挡在门外,不让狗狗进入医院大堂。
狗狗认为自己不是宠物,赖在门口,和保安人员对峙。
一个穿粉红色制服的护士走过来,帮我搀扶妈妈。
“狗狗,你回去。”妈妈回头,带着责怪的语气对狗狗说。
妈妈的话,在我们家,有如圣旨,是不可违抗的命令。
狗狗只好讪讪离开,随车回家。汽车有自动回航系统,无需人驾驶,狗狗回家不是问题。问题是我没有回家,一个人枯坐在这里。
我也不想一个人,可是穿粉红色制服的护士阿姨把妈妈带入诊疗室后,不让我入内,把我丢在大堂里。
大堂里这么多人,我乖乖地坐着,不惹任何麻烦,不与任何人打交道,井水不犯河水。像我这么守规矩的乖孩子,不想发生冲突,却偏偏遇上这个蛮横无理的白衣护士。
白衣护士阿姨咋咋呼呼的,让全部人都看着我,这是什么道理?
想到自己这么受委屈,不能不哭。
吧嗒吧嗒,地上一摊泪水。
那个可恶的白衣护士阿姨又走过来,手里牵着一个电拖把,像牵着一条狗。她放开电拖把,电拖把朝我冲来,停留在我两脚之间,咂吧咂吧吸去地上的泪水。
“哭!哭!就只会哭!你哭不要紧,地上湿了,别人滑倒怎么办?”
我捂住脸,挺直腰板,避免眼泪淌落地上。
白衣护士阿姨奚落我:“只会哭,不听话,大背包顶着后面,怎么坐?瘦瘦小小的,不吃饭,顶着大背包,不听话,只会哭......”
她说得我一无是处,我的眼泪又源源涌出。
“给你。”一只纤纤小手,拿着一张纸巾,伸到我面前。
我接过纸巾,擦眼泪,擤鼻涕。
好瘦的小手。